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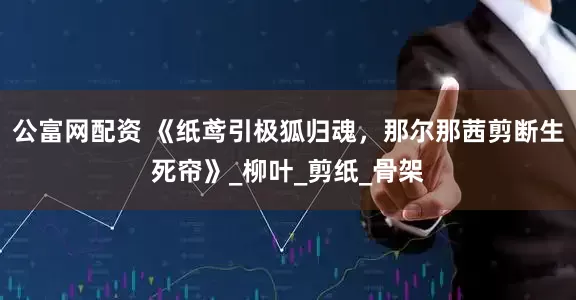
民国二十四年公富网配资,江南梅镇。
那尔那茜在春灯街尾开了一间不足十尺的剪纸铺。铺子没有招牌,只在乌木门楣上悬一只巴掌大的白纸狐,狐尾用朱砂点了一点,像一粒将落未落的血。镇上的老人说,那尔那茜剪的纸人能在夜里走动,剪的纸马能驮魂过河;可若你问她自己信不信,她只是低头用银剪裁出一弯月亮,笑而不答。
极狐死在这一天的小寒。
消息是傍晚到的——苏州河畔的仓库爆炸,沪杭甬铁路的特别列车被炸成两截,火一直烧到江面。极狐是沪上最神秘的“纸鸢师”,也是那尔那茜七年未见的情郎。传闻他能在风筝骨架里藏硝化棉,借东风送雷火,专炸日军的军火库;也有人说他本就是狐,借纸躯在乱世里渡劫。那尔那茜听完,只把手里正剪的“送子观音”折成两半,纸屑纷纷,像一场无声的雪。 当夜,梅镇落雨。
雨脚敲瓦,她取出珍藏三年的大红洒金纸,铺在案上。纸是她及笄时极狐送的,共七张,说将来若有一日他“忘了归路”,她便用这纸剪一幅“引魂”,无论他落在哪一处忘川,都能循纸而归。
展开剩余75%那尔那茜先剪狐形——头、耳、脊、尾,一气呵成。剪到尾尖时,她忽然停手,在灯下看那一点朱砂。七年前,极狐把纸狐塞进她掌心,说:“这点红是我心头血,将来若我死了,你点上尾尖,我便借你的眼再看一次人间。”
于是,她以针挑破自己左手中指,挤下一滴血,与那点朱砂重叠。血与朱交融,纸狐竟在案上轻轻一颤,像要抖落水珠。
第二步,剪“生死帘”。
这是最险的一步。帘由十二片柳叶形纸片连成公富网配资,每一片须在一呼一吸间剪成,多一息则断,少一息则滞。那尔那茜屏气,只听雨声与剪声交错,十二片纸叶落成,竟真的排成一列,像一道半透明的门。
第三步,扎纸鸢。
骨架用极狐当年留下的竹篾,轻而韧,可御九级风。她把纸狐缚在鸢首,再将“生死帘”缀在鸢尾,以发丝为线,一端缠在自己右腕,一端穿过狐心。
子时将至,她推门走入雨中,街灯昏黄,纸鸢在风里微微鼓胀,像一颗将醒的心。 梅镇西去三里,有古槐一株,树下是旧社戏台。相传戏台正对阴阳交界,三更鼓响,可闻鬼唱。那尔那茜立在台上,将纸鸢迎风一放,发线陡然绷紧,勒进皮肉。血顺线而下,染红纸狐尾尖。
雨忽然停了。
风从四面八方涌来,带着硝火、铁锈、焦木的味道。纸鸢扶摇直上,穿透云层。那尔那茜仰望,只见狐形在月下透出赤金光泽,像被重新点燃的星。
线的那端,传来极轻的震动。
她阖眼,视界骤然翻转——
她看见极狐站在苏州河畔的废墟里,左胸破开,却无痛色。他手里握着半截烧焦的风筝骨架,正抬头望天。天边,一只巨大的纸狐破云而出,尾带十二片柳叶,每一片都亮着微光。极狐笑了,唇形无声地说:“茜,借我一瞬。”
那尔那茜睁眼,发现自己仍站在戏台公富网配资,腕上发线却松了。纸鸢已不见,只剩十二片柳叶在空中缓缓飘落,每一片落地前化作白蝶,向四面八方散去。
她低头,掌心多了一张极薄的纸——
那是极狐的侧影,剪得极细,眉目却清晰。纸背有一行小字:
“身碎魂未散,愿归君红纸。”
次日,沪上报载:
“昨夜苏州河突现赤色狐形火光,自东而西,横掠江面,日军弹药库数处无端自爆,守军皆言闻狐啸。”
那尔那茜把报纸折成纸船,放进梅溪。溪水载着纸船远去,她转身回铺,取下门楣那只旧纸狐,在尾尖轻轻补上一剪——
原本向外的狐尾,如今弯成一个环抱。
后来,梅镇的孩子常在雨后捡到一种红色纸屑,状若狐尾,放在耳边,可听见极轻的男声念诗:
“我行过忘川,见杨柳、见硝烟,
见你在灯下剪一轮人间,
于是我用尽最后的硝烟味的风,
回到你指尖。”
那尔那茜活到八十岁,银剪从未离手。她最后的作品,是一幅巨大的剪纸,贴在春灯街尽头一整面老墙上:
一只纸狐,背负十二片柳叶,自战火中奔向一盏灯火。灯火下,女子低首剪月,腕上红线蜿蜒,像把一生的牵挂都系在风里。
墙下,常有旅人驻足。
他们问剪纸的名字,那尔那茜便答:
“此画名为——《极狐归》公富网配资。”
发布于:福建省迎客松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